被“规范”的人生,能否通过消解性别来打破?
- 资讯
- 2025-02-20 14:08:33
- 11
“性别界定”是人类社会身份认同的基本要素之一,从社会体系到社群关系,再到人际相处,性别都是一个人们早已习惯的界定标准。从出生到死亡,人的一生要填写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资料表,“性别”总是排名靠前的一栏。
但这种身份认同有时也会呈现模糊的一面或制造刻板印象,比如地铁女性车厢和女性停车位,就呈现着某种争议。一个驾驶技术出众的女司机或许会认为女性停车位意味着对女性的歧视,一个总是为了停车手忙脚乱的男司机可能会觉得女性停车位是对自己的不公平。同样道理,性骚扰的受害者固然绝大多数是女性,但当有男性也深受困扰时,那么将“性骚扰受害者”默认为女性的刻板印象,就会让这部分男性受害者无所适从。
在中国社会,这种刻板也无处不在。比如“男主内女主外”“男孩子必须有阳刚之气”,都是刻板印象的呈现。
也就是说,性别是人类固有认知的客观呈现,但如果将之视为一种不可撼动的规范,反而会在某些情境下制造束缚。
对束缚生活的规矩提出质疑,才会让生活有更多可能性
在《消解性别》一书中,朱迪斯·巴特勒借用福柯的理论,诠释性别束缚:“正像福柯说的那样,一个人必须屈从于一种控制性机器,以使得自由的行使能够成为可能。一个人要屈从于标签和名称,屈从于侵犯和侵略;一个人要受限于常态的种种标准;一个人要通过对自己的测试。有时候,这就意味着一个人需要变得对这些标准了如指掌,知道应该如何呈现自己,以使自己成为貌似合适的候选人。”
1956年出生于美国的朱迪斯·巴特勒是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专注于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领域,被视为酷儿运动的理论先驱。在《消解性别》中,巴特勒第一次将目光放在普通人和他们的生活上,批判男女二元的性别框架,反驳各种形式的性别本质论。
在巴特勒看来,性别规范有着两面性。一方面,如果没有一定的规矩,人们就无法相互理解和承认,但另一方面,让日子过不下去的正是这些规矩,因此唯一可行的做法是让性别这个概念保持开放性和不可知性。书中写道:“为了要生活,要好好生活,为了能够知晓朝哪个方向前进才会改变我们的社会世界,我们需要规范;但是,我们也会受困于规范,有时规范会对我们施加暴力,而为了社会公正,我们必须反对它们。”正如巴特勒所说:“批评的意义在于对束缚生活的规矩提出质疑,好让生活方式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消解性别》
在日常生活中,“男性特质”“女性特质”都是常见的话术,但它们并不是一种固定标准。你口中的定义和七大姑八大姨很可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而在网络上,这样的碰撞更是常见。也就是说,这些话术总会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即使是某些看似“约定俗成”的概念,也处于漫长的被制造过程中。
在这种情况下,“性别”的社会规范和一个完整的正常人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和束缚,甚至会衍生为政治问题。同性婚姻就是如此,正如书中所言:“政治是由可理解的话语构成的,它要求我们采取某个立场,不论这个立场是赞同还是反对同性恋婚姻;但是,作为人和严肃的规范性政治哲学及实践的一部分的批判性思考则要求我们探问,这到底为什么以及如何成为了一个问题——一个决定什么会、什么不会在这里成为有意义的政治问题。在现有条件下,为什么‘成为政治’的前景恰恰依赖于我们在话语性地构成的二元结构中操作(而不是探问)的能力,而且努力地不去知晓性领域就是被迫受制于对这些条件的接受呢?”
巴特勒继而将这一观点扩大到广义层面。她认为,如果将“理解”视为主流社会规范下的结果,那么“一定程度上的不被理解,并不是一件坏事”。
至于应对之道,书名的“消解性别”就是巴特勒认为的正解。她认为,“为了成全自己,我们就必须先消解自己:我们必须成为‘存在’的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以创造出我们自己。”当然,这一点也存在悖论,“当性别规范开始在不同层次麻痹性别的能动性时,这个悖论就会加剧。”
“消解性别”被巴特勒视为女性主义的重要基础。她的“酷儿理论”来自于李银河的翻译,英文即Queer,原意为怪异的、怪癖的。在她看来,没有任何性取向来自某种固定的身份,而是仿佛演员一般、不断变化的“协同表演”。基于这一理论,巴特勒认为性少数群体在社会中的孤立是“异性规范化”的后果,社会性别亦非天生生理身份的表现,而是人为规范化而成。
被规范的从来不仅仅是少数群体
虽然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着重于性少数群体,但若以为她笔下的“规范”仅仅针对少数人,那就低估了这本书的意义。
人类社会的“规范”,固然制造了基本秩序和伦理,但反过来也是对人类的限制。对于女性而言,规训更是无处不在。
在现代文明社会,多数正常人会接受与包容各种少数群体,并不将之视为“异类”。虽然狭隘的人与观念依然存在,但在人类历史上,这已经是特立独行者所面对的最好时代。
人类走到这一天着实不易,每一步都值得珍惜。仅仅在爱情层面,当人们习惯自由恋爱时,不要忘记就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盲婚哑嫁仍是主流,抗议不但无效,还会被指斥为忤逆不孝,挣脱家庭枷锁的年轻人面对的是千夫所指。
相比男性,女性选择离经叛道,前路会更加崎岖。哪怕到了17世纪,西方女性地位仍然极低,生活完全依附于男性,生活品质取决于丈夫的地位。要想衣食无忧,只有两条路径:或者生来是贵族,或者嫁给贵族。当有女性选择离开家庭、工场和教堂,离经叛道的她们面临的命运极为艰难。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边缘女人:十七世纪的三则人生故事》中就以三位女性为引线,借助各种档案、回忆录、自传、账本和画作等,剖析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生活。
书中的三位女性各有际遇。格莉克尔·莱布长于经商,写下七卷本自传,玛丽·居雅投身教育和慈善,玛利亚·梅里安是艺术家和博物学家。她们都是普通女子,但又并不普通。她们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谁的缪斯,她们从未淹没在母亲的身份中,也从未作为妻子而被抹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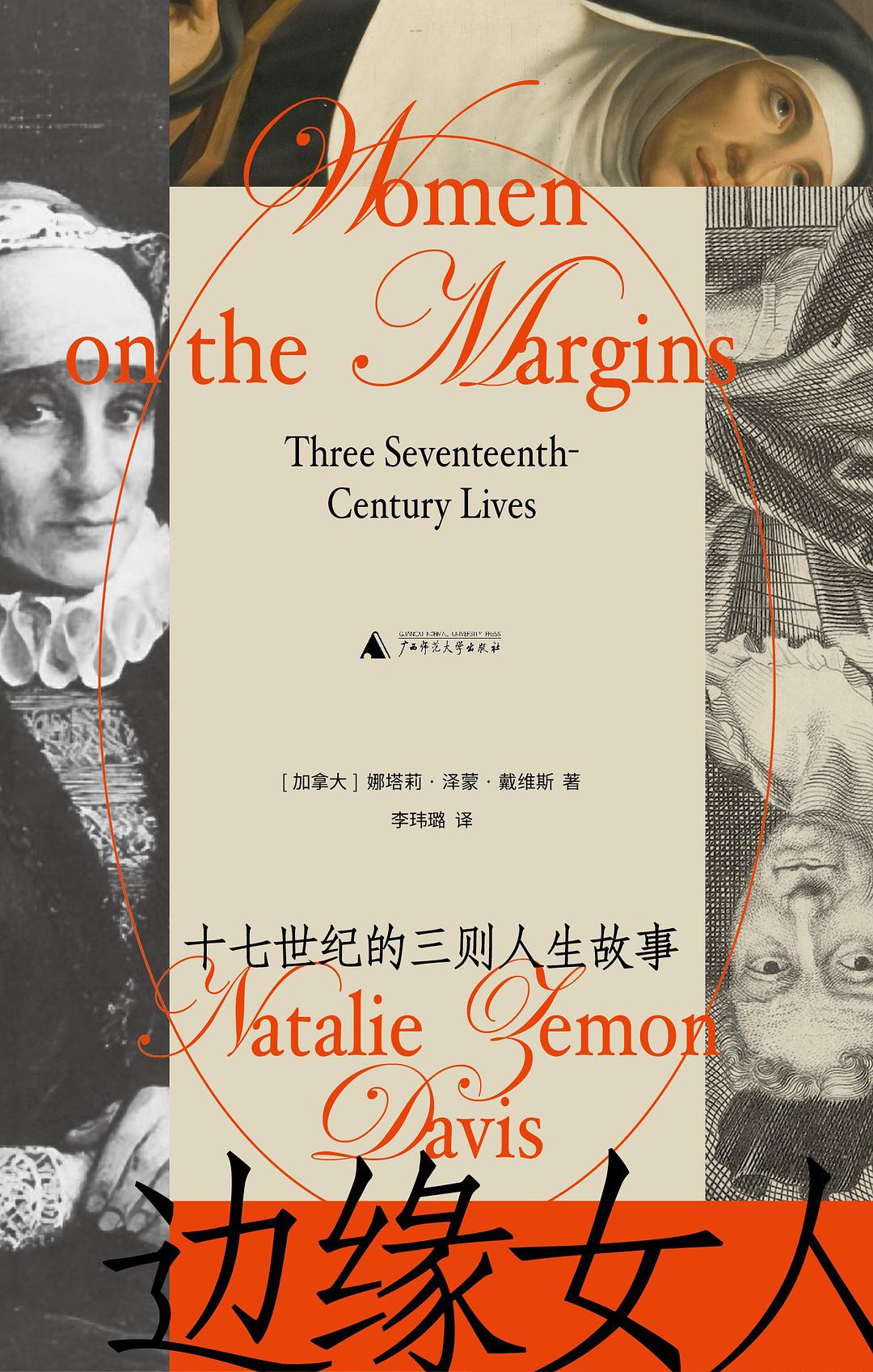
《边缘女人:十七世纪的三则人生故事》
玛利亚·梅里安精通水彩画和油画,还细心观察毛虫、蝇、蜘蛛及其他类似生物的习性。1692年,她因其离经叛道之举引发关注,“她抛下丈夫,前往魏沃特市的拉巴迪团体中找寻平静。”这只是人生转向的开始,“她将满载着标本从美洲航行归来,将出版她的伟大作品《苏里南昆虫变态》,将进一步充实她的《欧洲昆虫》,将成为阿姆斯特丹的植物学家、科学家和收藏家圈子里举足轻重的人物,直到1717年去世。”
格莉克尔·莱布的人生更难挣脱,她12岁订婚,14岁结婚,30年间生了14个孩子,之后成了寡妇。虽然孤儿寡母,但她却也因为这意外挣脱牢笼,利用手中家业,做生意、放贷,成为那个时代的强悍女商人。更可贵的是,她在自传中讲述了许多故事,以此教育自己的孩子。在17世纪,她的教育已经极为超前,努力呼唤孩子的独立性,将之置于父母权威之上。
至于玛丽·居雅,她的内心折磨与宗教有很大关系。从全书脉络来看,宗教影响着三位女性的选择,但并非决定性选择。她们分别是犹太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走上了同一条追求自我之路,并最终实现了自我价值,而且微微撼动了那个男性世界。
正是这三位在时人眼中离经叛道的女性,用自己的努力告诉世界:不管生在什么时代,被如何打压,遭遇多少不堪,“自我”仍然是作为“人”的最高追求。
但这样的人终究是少数,在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莫妮卡·贝鲁奇以绝世风姿成就了影史上的经典形象。但也正是因为这份动人心魄的美,才让影片尾声的摧毁美更加触目惊心。一个女性在战争期间的求生,在战后成了罪过,人们通过道德谴责弱女子,掩饰自己曾经的懦弱与不堪。
类似的事情在一战同样曾经发生。《女性史:20世纪卷》中写道:“成为妓女还是母亲?对于女性而言,性选择向来都介于两个极端对立的选项之间……在欧洲,对性的双重标准却带上了爱国主义的色彩……不忠的妻子被贴上了不爱国的标签,尤其是那些与战俘发生关系的人。她们在德国媒体上受到嘲弄,并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在法国,法庭对通奸的妇女实行严厉的判决,对杀害了不忠妻子的士兵却宽大处理。”
与此同时,女性养活自己并不容易。书中写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高昂的战时工资,而在报酬较低的岗位工作的女性为其他行业较高的工资付出了代价。传统女性职业仍然收入微薄,尤其是那些在家做工的女性。因为人们很难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最低工资法。”
从一战到二战,人们实际上都在面对同一个问题:“男人在外面丢的面子,回到家庭之后是要找回来的。面对战争也同样如此,在外受到创伤的男人,战后需要回到家庭重温其优越感。”
即使没有战争,在整个人类社会,这种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不少在外面打拼的男性,面对领导时唯唯诺诺,面对办公室复杂人际关系时忍气吞声,家才是唯一的宣泄渠道。因此,一战结束后,复员军人的家庭暴力事件多到触目惊心。
所幸的是,这并不是20世纪的全部。在人类历史上,20世纪是一个“女性”身份彻底被重构和确立的时代。女性从静默的他者和被注视的客体,慢慢在大众媒体的影响下开始融合汇聚,并在20世纪中后期到达了一个文化认同的高潮。在媒介传播的影响下,女性不再是世界一隅的孤立个体,而成为一个有着相似意识形态的集体。她们享有共同的审美爱好和世界观、价值观,具有更为趋同的女性特质,女性事实上由复数逐渐向单数收缩。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反抗着父权制的枷锁,但在资本主义和商业媒介的合谋之下,她们也越来越陷入了另一种单一身份的陷阱。
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乔治·杜比,主编了巨著《女性史》,“20世纪卷”是其第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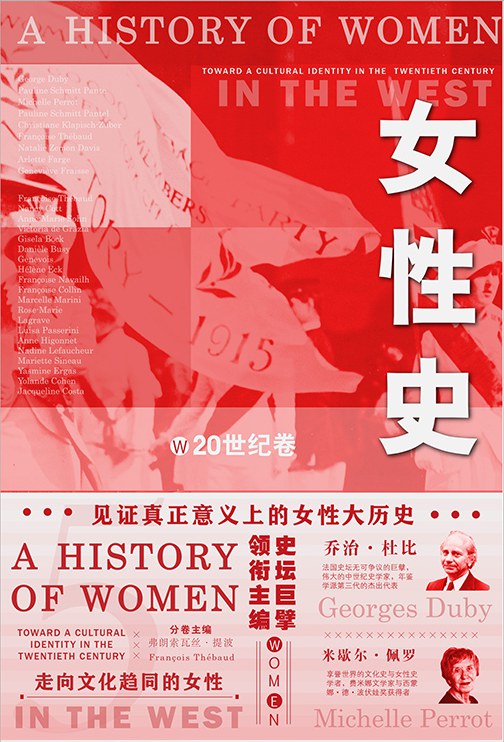
《女性史》
书中写道:“了解那些人生经历跨越了20世纪的女性,你将被她们的不幸和伟大所震撼。她们受到战争、革命和独裁统治的打击,也见证了两性关系的巨变。我们现在是否已经到达了女性史的‘终点’,到达了多年来稳定的、不可避免的解放进程的顶点?并非如此。如果诞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旋涡之中的20世纪地缘政治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东方集团瓦解后自由主义的胜利所带来的‘历史的终结’的概念,也未能幸免于欧洲及其他地区一系列事件的冲击。‘历史的终结’对女性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男性主导社会的末路和新社会黎明的到来?是一个性别分化几近消失的新时代?还是一个男性和女性既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特身份又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的世界?”
这些问题显然还没有足够稳定的答案,但变化显而易见。20世纪女性拥有和过往女性不一样的人生,取得的成就也是事实,包括投票权、生育风险的大幅降低、避孕措施和职场上的新机会等。
可这些“成就”同样是一种社会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有赞同和推动者,也有反对者,同时,没有任何成就是一劳永逸的。对女性进步运动的刻板认知,很容易让人忽视仍然存在的不公。审美层面的“规范”,也通过纤瘦的电影明星、模特和选美表现出来。
这导致“新女性”形象被固化:“她是一位专业的家庭主妇,既是家中的女王,又是精明的消费者。广告在贩卖商品的同时也贩卖图像。新女性看上去可能比以往的女性更加光鲜亮丽,但她们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广告同时也将女性自己变成了性对象和令人渴望的商品。”
被固化的女性,被“规范”的人生
对女性的固化,在婚姻层面呈现最为明显。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就写道:“婚姻市场对女性的局限性极强,比如说女性不能有过多的异性朋友,不能有过于频繁的社交活动,不能主动去追求性。一个主动的女生意味着她是婚姻市场外的‘社会女性’,不配作为结婚考虑对象,是被玩弄宣泄的对象。而一个男性在步入婚姻前与这样的‘社会女性’游戏,而到谈论婚姻时要求婚配的女性是白纸一张。这种风气往越小越偏远的地区越严重。”
上野千鹤子还曾写道:“对子宫的统治本来就是围绕出生婴儿的归属之争,这正是父权制的核心问题。”
如果探究问题的根本,那么上野千鹤子的另一个发问或许更为关键:“原本革命应当是不分性别的自由公民的解放,为何结果只是男性的解放,女性解放则被搁置了?”直至今日,它仍然没有答案。
在上野千鹤子看来,性别是太过明显的阶级对立,以至于容易被忽略。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被忽略甚至被“自然化”的对立无处不在。比如对性的看法就是如此,维多利亚时代的性伦理要求女性不能看也不能触碰自己的性器官,在这一要求之下,明明是自己的身体,对女性而言却是最为疏远的陌生之物。这样的伦理要求,直到今天仍有巨大市场,许多女性仍误以为对性的无知是“可爱”的表现,甚至谈“性”色变。
其实这一切的本质是经济问题,《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如同一把手术刀,所剖开的是近现代社会的性别经济结构。
成书时的1990年,正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开启“失去的三十年”之时,普通家庭无法承受高昂的市场化外包服务,因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全职妈妈。
全职妈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她们在家操持家务,却没有相应收入,许多男性回到家,往往还会来一句“你呆在家里什么也没干”。
这恰恰反映了父权制的经济基础,也就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这种统治的根本问题在于生产费用的不平等,比如男性在外工作养家,当然很辛苦,但如果将女性在家操持家务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对应为市场化费用(可以想想市场上月嫂和保姆的收入标准,还有教师的收入标准),很多男性的收入甚至无法承担这笔费用。与此同时,女性的牺牲也非常大,她们或者告别职场,很难重返,或者要牺牲事业,升职比男性更困难。
很多人或许会认为,这种比较并不合理,因为古代女性根本不出去工作,“男主外女主内”是传统,如今的全职妈妈,或者职场女性的家庭付出,不过是对传统的继承,并不是一种新的剥夺。这个说法当然是荒谬的,因为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依托,就是机器化生产、市民社会和教育普及,它必然使女性能够接受教育、参与社会事务并参与社会生产,也必然会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所谓传统。但与此同时,父权制的存在,使得男性多少成为获益者,往往可以享受女性“内外兼顾”所产生的剩余价值。
现代社会继承了传统社会的一种观念,即刻意强调女性的爱与母性。这种将女性推上神坛的价值观,几乎已经成为教科书一般的真理。但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这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既然爱是“无条件付出”,母性是“隐忍和牺牲”,那么就可以等同于无价值劳动。它们看似对女性的赞美,实际上遮蔽了女性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
即使无数人曾提出女性的“自主权”,但正如《消解性别》中所言:“任何一个自主权的概念都有着局限。自主权实际上是在社会条件制约下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方式。那些社会工具可以赋权,但也具有约束力,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功能同时发挥着作用。”
不管是否认同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提及的“规范”,都不能回避这样的事实:“规范就是那种决定了‘可理解的’生活、‘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的东西。如果我们违背这些规范,就很难说我们是否还能生活下去、是否还应该生活下去,我们的生活乃至生命是否还有价值、是否能变得有价值,我们的性别是否是真实的、是否能被看作是真实的。”
上野千鹤子所批判的父权、所揭露的女性被剥削的隐藏事实,都以这样的“规范”而呈现。具体在社会层面,它被渲染为“女人一定要结婚”“不生孩子的人生就不完整”等常见话语。无数人选择“适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解性别》中提到的解决方案并不可行。事实上,开放的心态和认知,永远是人类进步的倚仗,在性别问题上同样如此。
下一篇:蓬勃生长,河北跨境电商聚新成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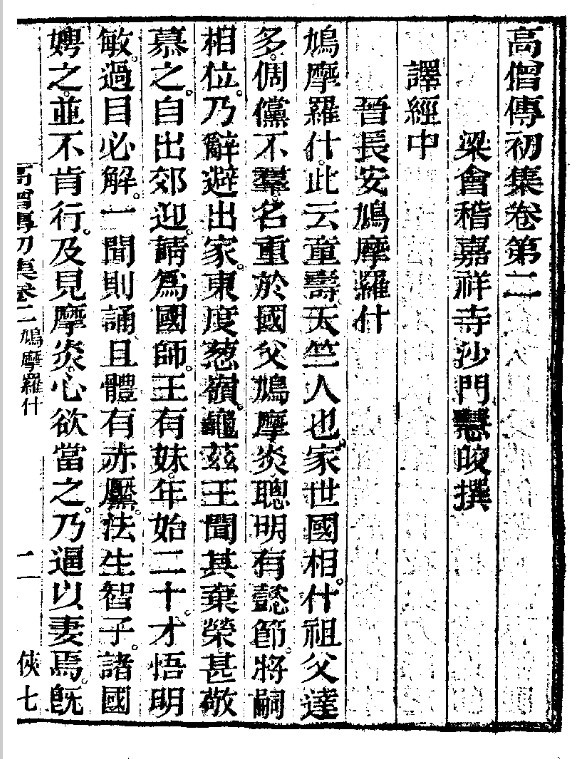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