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丨时光深处那“年”
- 情感
- 2025-01-24 21:30:09
- 11

妹妹从四川打来电话,给我寄了腊肉腊肠和水果。她感慨:“小时候,腊月二十三已经算过年了……”和妹妹聊着,思绪便逆流而上。红墙木门的四方小院仿佛就在身后,回头,阳光依旧灿烂,枣树上挂着干菜,母亲沾了两手面粉,她边系围裙边招呼我:“过来烧火。”
我坐在灶膛前添柴,火苗舔舐锅底,欢快而热烈。锅里蒸着糕窝窝,热气裹挟着香甜氤氲出来,我咽口唾沫。每年,父亲都会开辟一小片地,种上黍子,只为过年这一锅糕窝窝,春节专属,全家最爱。刚出锅的糕窝窝很黏,放哪儿粘哪儿。母亲便把高粱秆剥光,用竹签一根根串起来做个大篦帘,糕窝窝摆上去,一排排色泽金黄,点缀着红枣,香甜软糯,不仅馋坏了我,也馋坏了那位老婆婆。
老婆婆是过路人,走累了,来我家讨水喝。母亲从锅里舀了热水,又拿个糕窝窝一并递给老人。我和妹妹都还没有吃一口呢!我们俩对视一眼,有点鄙视老婆婆。村里家家户户都在蒸过年馒头,偏偏来我们家喝水,不过是闻着味道,奔糕窝窝来的。母亲看出我心里不满,轻轻用手肘拐了我一下。
老婆婆吃完一个糕窝窝,眼睛一下一下地瞄向篦帘,母亲喊我:“给奶奶再拿一个。”虽不情愿,我还是给了她一个。母亲问老奶奶:“是走亲戚吗?”“是还愿。”我们家往南不远有个旧庙故址,附近的老人把美好愿望寄托在许愿上,年底不管愿望有没有实现,都会去上一炷香,还一下愿。
吃饱喝足,老婆婆站起来要走不走。母亲噗嗤笑了,用白纸包了两个糕窝窝放到老婆婆手里说:“大娘,路上饿了吃。”老婆婆真感动了,她拉着母亲的手唱起祝福经来:“腊月里二十三呐刮北风,遇到了好人我心高兴,你们一家人都行好运,神仙保佑小花容成大学生——”母亲笑得更开心。我拉拉母亲衣袖:“啥是小花容?”母亲说:“你啊!你就是小花容!”我也笑,前仰后合。
蒸完糕窝窝,要蒸枣馍馍,黄豆和大枣馅儿的,然后蒸包子。这时候我和妹妹有点不耐烦了,便问母亲:“还蒸吗?这么多,吃得完吗?”母亲轻轻打我一下:“过年不许乌鸦嘴。”我纳闷,说什么了就乌鸦嘴?为了佐证没有乌鸦嘴,我又试探着说:“蒸这么多馒头,吃不完!”母亲用沾着面粉的手捏我嘴角:“过年不许说多啊少的,不吉利。”
这有什么不吉利?但我不敢再问。母亲一边包包子一边解释:“咱这儿讲究大年初五之前不能动刀动案板,所以要蒸够初五前吃的干粮,家家户户都这样,不信你去看看。”我便跑到前后左右邻居家看,家家户户院里都放着一只大瓷瓮,蒸好的馒头包子一股脑倒进去,这就是北方农村的天然“冰箱”。
天上飘起雪花,越来越密。从邻居家出来,我站在小村里,听鞭炮声四下响起,孩童欢呼,鸡犬相闻。雪刚刚好,薄薄一层,小村便粉妆玉砌。仰头,一缕缕炊烟扶摇直上,如诗如画。过年在那一刻变得具象。这景象成了后来怎么也达不到的美好。
村里老年人大多信神,家家供关帝爷、玉皇大帝、观音菩萨等。母亲说:“我也不知道烧香管不管用,老辈子留下来的习惯,总不能在我这儿断了。”除夕那天,新换的神码上要贴“嘎嘎纸”。我觉得“嘎嘎纸”的叫法很搞笑,但着实好看。深红浅绿鹅黄各色纸张剪成石榴花、荷花、蝴蝶、万字等花样,两边剪着飘带,覆盖在神码上,风一刮,神码若隐若现,增添了些许神秘,也让“神仙”看起来柔软亲和了很多。
我和妹妹唱着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便到了除夕。
农村的除夕不像城里那般散漫。几十上百年一起生活在这里,大家的习惯是同步的。上午贴对联,下午包饺子,晚上守岁。
父亲只贴对联,不管贴神码。母亲说:“贴好对联顺手的事,神码就贴上呗。”父亲嗤笑:“我不信那个,不贴!”过年,母亲不和父亲吵架,她便带着我们贴神码。父亲不愿意干的事儿,却是我们几个感兴趣的。给神码刷上糨糊,恭恭敬敬贴在神位上,外面覆上“嘎嘎纸”。剩余的“嘎嘎纸”便到处贴起来,柜子上、门上、树上,墙上……家里焕然一新,连心情也雀跃起来。
小村的年和饺子密不可分。
母亲擅长包饺子,我更擅长擀饺子皮。母亲说:“谁擀皮谁和面!”我老是掌握不好面粉和水的比例,和的面要么硬邦邦要么软塌塌。母亲说:“反正你擀皮,软硬自己掌握。”
那次,面和得太软了,擀起来倒是快很多。饺子皮一摞一摞堆到母亲面前。母亲包着饺子和我说着往事,母慈子孝。逐渐母亲不吭声了。我又擀了一摞,往前一推,刚想炫耀擀得快,一坨面疙瘩飞过来砸我脸上。母亲生气地指责我:“你看看这面,稀软!还没包就沾在一起,下锅一煮就烂。大过年,吃片儿汤?”我一抹脸,摸了一手面粉,抬头气愤地瞪母亲。应该是我脸上沾的白面很滑稽,母亲忍俊不禁。我越发委屈,擀面杖一扔,不干了!
母亲笑够过来哄我:“好了,是我不对,不该用面疙瘩砸你!”母亲一说,我更气,眼泪下来了。能感觉到母亲拉我的手在颤抖,她还在笑。“不生气啊,大过年的,生气一年都不好!”母亲重新和面,然后像在求我:“快来擀皮吧,你听,别人家都在放鞭炮了。”果然有鞭炮声响起,这意味着有人家开始吃年夜饭了。
我们村庄有个不成文的竞争机制,比谁家年夜饭吃得早,越早证明这家人越能干。我很在乎这个,便抹干眼泪继续擀皮,一边嘟哝:“谁家过年用面疙瘩砸自己闺女!”母亲又开始笑,乐不可支。我也跟着笑了。
妹妹在电话里问我:“姐,你笑啥?”我惊醒,才发现自己沉浸在回忆中。“没事儿,想起来小时候过年了。”妹妹轻声问:“想咱妈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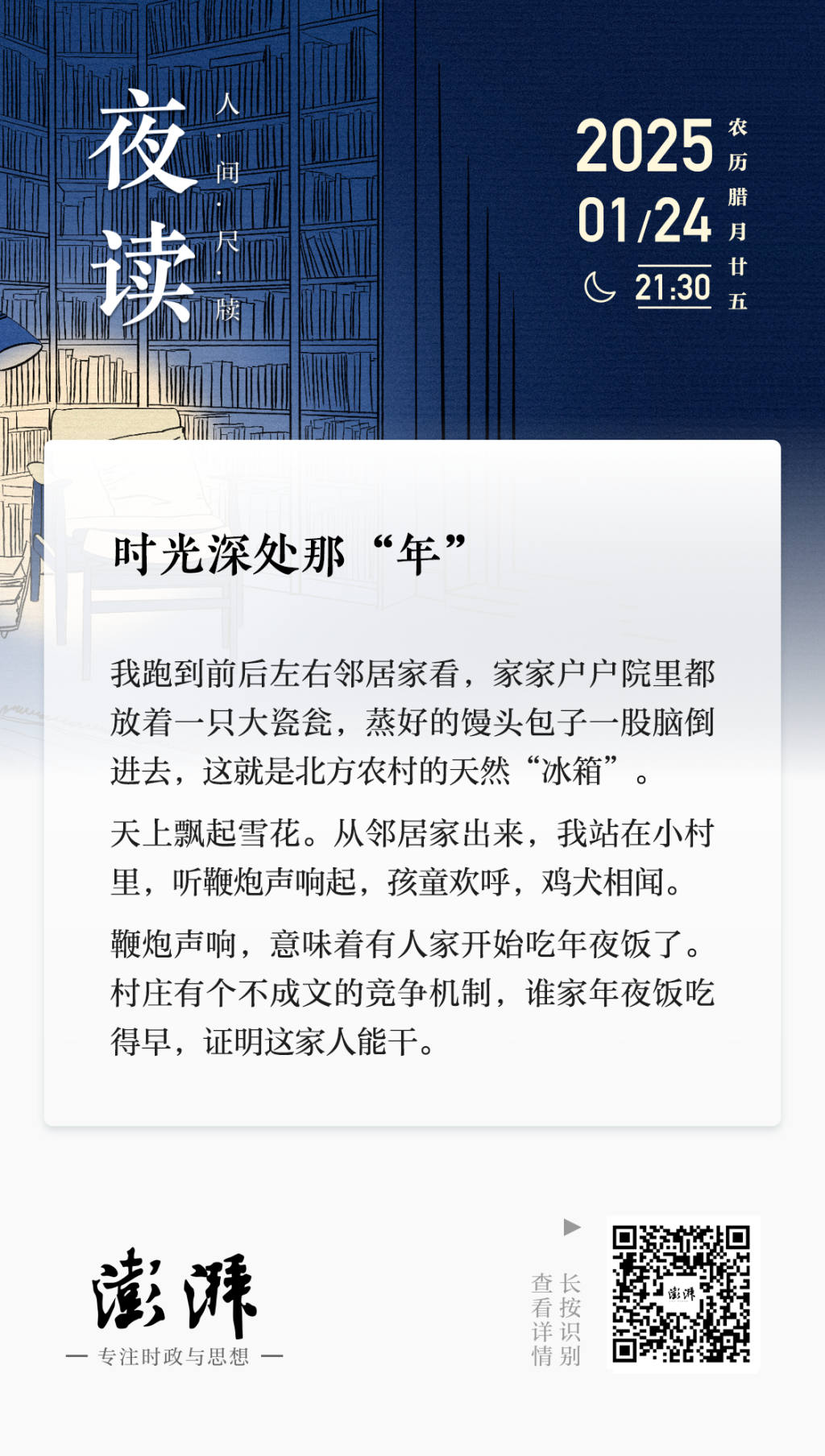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