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为什么在物质生活充裕的当下,人们的精神内耗频发?对于20世纪以来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学者从生活变化、传统丧失、人际疏离各方面给出过解读。心理学家荣格认为,过多的不假思索的对社会成就和实用性的追求会令人们的心灵干涸。奥地利神经与精神病学教授弗兰克尔发现了一种“存在的真空”:人们不仅缺乏直觉,还要忍受传统丧失的痛苦,面对生活茫然无措。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则认为,现代社会的人格通常是自洽的、严格自我控制的,而这样的意识阻断了人类的情感以及朝向他人的本能冲动,最终消灭了这样的冲动,这正是现代社会孤独与情感隔离普遍出现的原因。
从日前出版的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埃伦贝格的《疲于做自己:抑郁症与社会》和古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生存的艺术》里,我们或许也可以找到为现代人精神苦闷开出的药方。
“一切皆有可能”的暗面
《疲于做自己》一书提出,抑郁症的普遍发生与独立自主的个人成为社会现实有关。忧郁症与抑郁症相似又不同,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自我意识锐化到极致的不幸产物,但忧郁症更多属于出色之人,抑郁症的出现则像是民主化和大众化的产物。阿兰·埃伦贝格认为,抑郁症流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整个社会机制的变化催生,由富足而非经济危机引起。

[法]阿兰·埃伦贝格 著 王甦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2025-2
埃伦贝格将抑郁症的蔓延与“一切皆有可能”、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样的思潮相联:因为现代人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创造历史的机会,不应该像过去一样接受宿命的安排、苦难的折磨,所以人们让自己动了起来。

现代社会中,我们面对的不是公共生活的衰退,而是各种参照系都在普遍个人主义和开放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寻找自己的位置。埃伦贝格写道,对于个人的要求也发生改变:个人不再依靠外部指令行动,而是被要求求助于自己的内在,依赖自己的思想能力。在职业生活或个人生活中,制定计划、发挥能动性、加强交流成为了普遍规则。
《疲于做自己》追溯了工作生活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工作的投入度有所提高,稳定保证却显著减少,对于工作的要求也有所改变,管理的重点不再是驯服身体,而是调动每个员工的情感和精神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焦虑情况、心神疾病和抑郁状态渐渐变多,埃伦贝格由此指出,企业可谓生产神经性抑郁症的“门厅”。
对于精神自由和能动性的强调,消解了稳定和确定性。人们被许诺自由和解放的人们,却不具备足够的力量,“他脆弱、缺乏存在感,因自己的主宰力不足疲惫不堪、怨声载道。”因此,抑郁症如同更平等的忧郁症,是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人们无法避免的反噬。通过抑郁症,人们看到“尽管限制和自由在改变,人类无法缩减的部分并没有减少”,抑郁症是因为人们必须要忍受“一切皆有可能”的幻觉才会产生。
追求不自由
尽管荣格、埃利亚斯以及还有埃伦贝格都认为焦虑、抑郁来源于变化的现代生活,可是人们的苦恼未必是从现代开始的。埃伦贝格笔下想要获得一切的个人,与古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谈论到的烦恼个人具有相似之处。在风险和机遇并存的生活中,人们应当如何才能做到幸福和平静?学会如何区分能力之内与能力之外的事物是最重要的。
“每当看见一个人饱受焦虑之苦,我就会想,天啊,他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他不把目光放在自己能力控制之外的东西上,他的焦虑就会立刻烟消云散。”爱比克泰德这样区分两类事物。人们的认知、动机、欲求、厌恶属于能力范围之内的事物,而身体、财产、名誉、官职都属于能力之外的事物。爱比克泰德认为,追求那些“不自由”的事物是人们不幸福的原因,“如果你把天生受奴役的东西当作自由,把别人的东西当作你的,那么你将会受挫、悲伤、陷入混乱。”不仅是对于官职和财富的欲望会让人卑躬屈膝和受制于人,想要四处旅游、获得学术知识的愿望,也会使人们受制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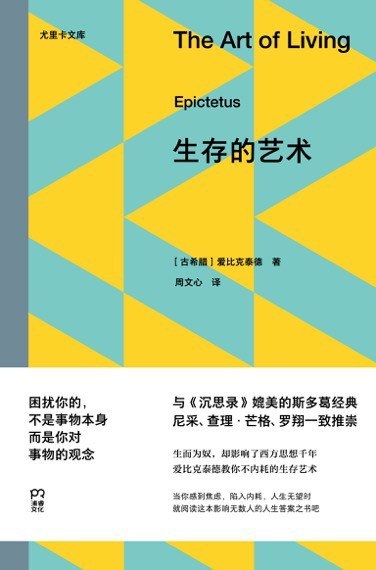
[古希腊] 爱比克泰德 著 周文心 译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4-10
一个人要是一直提心吊胆就不可能自由,谁摆脱了恐惧、痛苦和焦虑,谁就获得了自由。爱比克泰德说,人们应当学会从自己的意愿出发,辨别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这就是教育的意义。所以接受教育,不是为了改变事实,而是为了知道我们关心之物的本质,并保持意志与事物的本质一致。人们应当尤其重视培育自身的意愿,将它培养得自由、高贵,与自己的本性保持和谐,而并不需要和他人一模一样。退一步说,如果不得不出卖自由意志,爱比克泰德提醒道,“考虑一下,多少钱会让你出卖自己的自由意志。如果一定要卖,请勿贱卖。”
虽然出发点与以上作者并不相同,弗洛伊德也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反思了现代文明的问题。他的观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对于文明的敌意始终存在。“似乎可以肯定的是,生活在当今的文明中,我们并不感到舒适,”弗洛伊德写道。文明在保护免受自然侵害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在调节人类的关系之时显得困难重重。因为用群体的力量来取代个体力量的本质是“群体成员限制了自己得到满足的可能”,也就是限制了个体的自由。有意思的是,弗洛伊德还特别指出,尽管人们想要否定这一点,但人类并不是温和的动物,反而充满冲击,如果这种攻击性没有得到满足,人不会感觉舒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某些“敌对面”总是需要存在。举例来说,就像罗素写过的,地铁上的人们需要压抑自己的动物本能才能在高峰期与这么多陌生人共处,而这种压抑难以避免地变成了一种扩散性的愤懑。弗洛伊德寄希望于,如果我们可以用一种方便无害的形式满足进攻性倾向,比如将敌意化为嘲弄,群体的团结和亲和度也可以得到提升。
















有话要说...